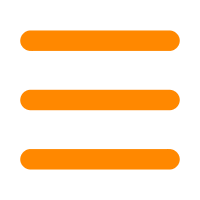本文分别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法性、实效性和逻辑性三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质疑,并从治标和治本两方面对新时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重塑提出了立法建议,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字:坦白、抗拒、沉默权、选择权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中国早已是妇孺皆知,曾几何时,这一刑事政策的颁布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积极有哪些用途。然而,伴随国内司法理念的改革和法治的不断健全,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不久前召开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正式载入宪法,于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被推到前沿,大家开始重新审视存续已久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理性,愈加多的质疑渐渐凸现。
1、什么时间置疑
(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法性”
所谓“坦白”,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其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或有关组织发现后,在被传唤、讯问时,或者在被采取强制手段将来,或是法庭审理过程中,如实交代其所犯罪行的行为。“从宽”顾名思义,应当是量刑时的宽大处置,具体应当包含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三种状况。所谓“抗拒”,系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如实回答司法机关或有关组织的讯问,采取不予配合的态度,它包括不坦白和假坦白两种情形。“从严”即为从重、加重处罚。
依据国内新刑法就量刑问题的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应当依据犯罪的事实、犯罪情节、犯罪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害处程度等原因进行综合考量,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论处。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法原则中常见推行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纵览国内的刑法总则,对量刑规定的条约主要在第四章,其中明确规定将自首和立功作为法定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从而形成了完善的“自首立功规范”。但该章节并未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坦白亦或是抗拒)明确规定为法定量刑情节,故在司法实践中总是只能将它列入酌定情节予以考虑,因为新刑法修改了原刑法59条第二款的规定,取消了一般法院酌定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权力(除非因案件特殊状况,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自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便成了一句空话,既然现行的刑事法规中对此没作出明确的规定,从“罪刑法定”的原则出发,“从宽”和“从严”都缺少有力的法律依据,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合法性”。
(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实效性”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口号对很多中国人来讲耳熟能详,由于它过去伴随中国司法规范走过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在威慑罪犯心理、加速案件审理过程中立过汗马功劳,它的意义和影响从几代垂髫小儿打游戏的雷同口号中可见一斑。
然而,在这一政策一次又一次的被反复适用的过程中,也同时一次有一次地被扭曲,被滥用。以至于在社会上曾一度流传了如此的说法:“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春节。”如此的一种歪曲的形态反映了一种司法的“悖论”:国家鼓励坦白,但坦白后将被定罪,并可能判处重刑;法律禁止抗拒不供,可那些无视法律的奸猾之辈却也会因证据不足而逍遥法外。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既然坦白未必从宽,抗拒也不当然会从严,那样,提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则是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误导或诱导。坦白从宽就成了变相的诱供,抗拒从严即成了逼供的翻版。
也就是说,这种“悖论”导致司法职员的一种道德困境。法律和司法伦理禁止对任何被讯问人的引诱和欺骗,以不合法并违背司法伦理的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在法律上无效。而回顾多年来的司法实践,大家的司法职员以“从宽”来感召嫌疑人坦白,“从宽”的许诺可以使用不一样的方法,如明示的、暗示的、模棱两可的,但最后却不可以兑现这种宽缓的承诺时,它在客观上就等于诱供和骗供。很多案件没口供定案十分困难,被告可能因此而逃脱法律的制裁,司法职员为达成办案效益总是容易作出较大宽缓的许诺以最大限度的获得口供,但嫌疑人供述后所达成的从宽幅度比较有限,甚至是根本没办法达成的。假如许诺与实质后果明显脱节,就不能不叫人质疑到取证的合法性问题了。
长此以往,“司法”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对口供的过分依靠,导致了审讯职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采取过多不合实质的许诺,但最后总是不可以兑现。保全了一个案件的认定,却付出了更大的本钱,在这背后牺牲的是国家刑事政策的公信力,和法律的威严紧急缺失,这样巨大的社会本钱何以承受。显然该政策的实行并不可以达到预期的社会成效,反而带来了更大的问题。
(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逻辑性”
“坦白”与“抗拒”都是在“有罪推定”原则下的表述,也就是把每一个犯罪嫌疑人潜规则里设定为“罪犯”,而现代司法文明是倡导“无罪推定”的,是把嫌疑人假定为无罪的基础上推理、断定。目前国内刑法已将“无罪推定”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那样在这个基本原则的引导下,对一个未经法院宣判的犯罪嫌疑人来讲,所谓的“坦白”和“抗拒”又从何而来呢 ?
[1][2]下一页